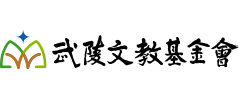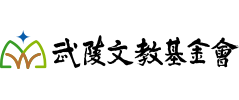跨國電話、漂流瓶、回聲與信
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
徐嘉恩
【得獎感言】
謝謝媽媽和外婆,是你們的情感賦予這篇散文色彩,謝謝怡君老師,初次嘗試散文,尚有許多不足,謝謝你的鼓勵和指導,讓我得以將思想寫入現實,也謝謝主辦方,讓我的文字得以被看見。
文字是我表達自我的語言系統,我連結世界的交流方式,在我的非程式語言裡,每一次敲下新的字元,就是在對世界說你好。
希望回憶的長風把思念和感謝吹到我們生長的地方,替我向家打聲招呼。
【得獎作品】跨國電話、漂流瓶、回聲與信
「你外婆就留了這麼幾張照片,好多年前了,你都不記得了吧。」偶爾,母親會心血來潮的翻開舊相冊,重溫一遍過往時光。我和她一樣有些戀舊,沿著回憶的
海岸徐行,踩在殘缺的足跡上,潮起潮落間就捲走些許遺憾。
我拿起一張外婆在前庭拍的照片說,我記得。
回憶是一封沒有收件地址的信,紙短而情長,是浸在水煙裡濕潤的字跡,筆耕不輟的寄件人與模糊不清的收件人。
「煙斗不都是小小的,像電影裡抽的那種。」年幼的我比劃著認知中的尺寸,再裝模做樣的擺個電影明星的同款姿勢,「為什麼外婆的煙斗這麼大?」
「不是那種煙斗。這是他們雲南的傳統啦,叫水煙筒。」母親寬厚的手梳過我的頭髮,溫聲回應。
她用「他們」這個詞,似乎是種糾結的命運,我們三代人,留著相同的血卻在不同的地域生根發芽。
害怕菸味,我站的離外婆遠了些,看她在半人高的水煙筒中吞雲吐霧,短管處的菸絲燃起一點星火,瀰漫的煙與水氣橫貫我與外婆之間,在我仰望的目光中翻湧。
近於赤道的陽光贈予她黝黑的面龐,高山的風雨切割出堅毅的棱角,而此刻,矇矓的煙柔化了她的剛強,襯出幾分溫柔和藹。我隔著水霧看她,像瞭望雲霧籠罩的遠山,只有那雙矍爍的眼睛如飛鳥,破雲而出,穿透世代的帷幕回望我。
如同外婆留給我的記憶一般,總是清晰卻碎片化的細枝末節,其餘的大部分都矇在一片水幕之後,連同她的身影一起失真,又在某些不經意的時刻浮上水面。就像散落在家裡、乘載情感的物件,時間的積累讓它們沉澱到更深處的角落,彷彿隱沒在岩層之下的化石,等待著被發掘的一天。
大掃除使我成為一位以家為起點的考古學家。我踩上椅子,從積灰的書架上取下一柄掃帚,竹編的、不到我手臂長,握在手裡像小孩子扮家家酒用的玩具。
「這還在啊。」母親拿著拖把經過時說,兜裡的手機正外放著泰語節目,隨著她的移動路徑在我耳邊忽大忽小的演繹。
這還在啊。我也在心裡跟著感嘆。
同樣的前庭,外婆手裡的水煙筒換成了編織中的掃帚,我盤腿坐在堆滿作物的磁磚地上,學著外婆的手法,將堅韌的枯草與果樹遺留的枝葉纏繞在一起,像支號令山林的權杖。
我終是沒學會這項手藝,可靈魂的底色卻留下了烙印。星空下,山野中,村裡不停歇的歌舞與炊煙,五彩斑斕的文化在這片豐饒的沃土上生長,天際線不只是高樓大廈切割的方正線條,土地上不只有鋼筋水泥砌成的樣品屋,外婆家的夜晚會有星星。
在我專注於揀漂亮的樹葉來妝點時,掃帚的工序已經進行到了最後階段,外婆拿紅繩在握把頂部繫上一個結,揮揮手招呼我過去。
那是把對於大人而言稱得上小巧玲瓏的掃帚,於年僅四、五歲的我而言卻是恰如其分。我握著掃把,抵著地面轉了幾圈,為四周清出一塊空地,外婆看著我笑,像在滿意她的傑作。
長大後再回想,說不定她也看到了三代人童年的縮影,看到戰火紛飛下如翅果翩飛的自己,看到物資匱乏下如勁草蔓生的母親,也看到和平年代下向陽生長的我。
興許是對貧瘠往年終究結出碩果纍纍的釋然,與生命達成了和解。
時間的線性敘事從相同的血脈流淌而過,從雲南到清邁,從清邁到台中,是擁抱時交融的呼吸,手心相覆時交疊的生命線,跨越世代的鴻溝塑造同一雙面向未來的眼睛,一如外婆穿透水霧注視我的目光,在她瞳孔的倒影裡,我也用那雙近似於母親的眼眸回望她。
「我們上一次回泰國是什麼時候?」我問,手撫過掃帚的紋理,柔韌的材料被編成結實挺直的手柄,長年的擱置也不損它分毫。
「好久了啊,上次回去你才這麼小。」母親比了一個不及腰的高度,對比我已經比她高出不少的身高,看上去有些滑稽。
一個踮起腳尖才摸得到門把的年紀,對死亡的意義一知半解,對變成星星的說法還深信不疑。但迷茫難過如波濤洶湧,尚未學會掌舵的年輕船員在鋪天蓋地的浪潮中迷失自我,只能緊緊抓住母親衣角,祈禱不會在風浪中翻覆。
可母親的眼淚卻是風暴來臨的第一滴雨,泛紅的眼眶和哽咽的哭腔才是我行駛不過的漩渦。
一通跨國電話如遲來的春雷打破夏夜的平靜,相隔兩地的相安無事、蟄伏在皮膚下的複雜情感迎來了它此生第一次驚蟄,電話的另一頭有同樣的哽咽,有安慰,有錯亂的腳步聲,有壓抑的、顫抖的呼吸,唯獨不會有外婆的聲音。
唯獨不再有水霧間烏黑堅定的眼,一點觸手可及明滅的光。
死亡宣告只需要一通跨國電話,思念卻是海中隨波逐流、找不到陸岸停駐的漂流瓶。
我應該在泰國山上和外婆數星星,我應該為她再掃一遍前庭,我應該跨越煙霧給她一個擁抱,而不是在遙遠的台灣收到一張無用的不在場證明。
我應該不要那麼痛苦,因為我的悲傷絕不及母親的千萬分之一。
此後每一天,當她走在外婆家那條曲折的黃土路時,日落時分,爐灶炊煙,不同戶人家此起彼落的叫喊聲中,誰來喚她回家?
「你們小娃兒是不是就喜歡跳著走?」回憶裡外婆問。
她說中文時常講雲南方言,我憑直覺回應總不會錯,若仔細思考語句反而難以理解,這是一種本能,語言系統裡的刻骨銘心。
而就如同我當初手舞足蹈的問煙斗的大小,外婆也身體力行的問步伐的躍動。
她模仿我的走跳,年老的身軀迸發出童趣的活力,我為她誇張的動作在身後笑的上氣不接下氣,再急忙的追上大人寬大的步距。
家的輪廓已經浮現在彎曲的山路盡頭,像遇到斜坡就迫不及待衝刺的孩子,我們也跑跳著奔向不遠處的家。
一步、一躍、一走、一蹦,踩在被夕陽烤成橘紅色的黃土路上,微微濺起的塵埃附著在鞋上,落日是山林短暫的秋,入眼所及皆鍍上一層暖色調的光。
我聽見風捎來母親的呼喊,我的泰語名字,我的血緣紐帶,我的來處與歸途。
她又喊我「姑娘」,兩個字在雲南話裡都唸一聲,和女兒同義。之後的語句混雜著方言、泰語、中文,我零零碎碎的拼湊出快回家吃飯的含義,大聲應了好。我又接著喊,學著外婆與母親的口音喊一句四不像的「快到嘍」,樂不可支的人就從我成了她們。
山谷迴盪著我們的聲音,歷久經年不衰。
記憶定格在有些缺氧的奔跑上,歸途的風從我衣領間蕩過,一步、一躍、一走、一蹦,就踏過三千多次日落,兩千多公里,十年光陰,歲月如梭。
於是十六歲的我放下手中的照片,笑看著母親說:「再等兩年,等我畢業,我們一起回家看看吧。」
回家,我咀嚼著這個詞。
回家吧,這才是跨國電話、漂流瓶、回聲與信都不曾擁有的溫度,親自去聽群山中是否還有過往世代相互交映的回響,張開雙臂,歸途有風。
【評審評語 ◎劉克襄】
透過雲南外婆手握水煙筒的吞雲吐霧,以及製作特有的地方掃把,作者悉心地懷念過往跟她種種相處的時光。母親則在其間,允當的扮演協調之角色。
一個家族三代不同的女性,在不同的時空,各自有觀看世界的哀愁和愉悅。有此書寫,生命的告白終得抒發。祖孫間因地理隔閡的遙遠和疏離,似乎也能透過點滴生活的回憶有機連結,串出綿密思念的情愫。看似平淡的散文,對回家的定義,卻有一不俗的表述。